
最新文章导读
往事如歌
| 我在伐木队当医生[梅怀礼] | 17-11-23 | ||||
| 医者仁心[陈瑞琳] | 17-11-23 | ||||
| 我做过的几件[赵中越] | 17-03-11 | ||||
| 我的回忆[孙都军] | 16-12-24 | ||||
| 木工之家[杨金德] | 16-12-24 | ||||
| 我在加工厂的40年(二)[张安民] | 15-12-19 | ||||
| 我在加工厂的40年(一)[张安民] | 15-12-19 | ||||
| 回忆录[侯式川] | 15-12-09 | ||||
| 历经北风[夏志中] | 15-12-09 | ||||
| 怀念校友、战友、荒友曹德麟同志[陆文灏] | 15-11-28 | ||||
| 令我终身难忘的四位开国元勋[陈瑞琳] | 15-11-28 | ||||
| 回眸(节选五)[许凤岐] | 15-11-22 | ||||
| 回眸(节选四)[许凤岐] | 15-11-22 | ||||
| 回眸(节选三)[许凤岐] | 15-11-22 | ||||
| 回眸(节选二)[许凤岐] | 15-11-19 | ||||
| 回眸(节选一)[许凤岐] | 15-11-19 | ||||
| 回忆录(节选二)[唐佽] | 15-11-14 | ||||
| 回忆录(节选一)[唐佽] | 15-11-14 | ||||
| 农场难忘岁月——回忆录(节选)(六)[高诗钢] | 15-10-30 | ||||
| 农场难忘岁月——回忆录(节选)(五)[高诗钢] | 15-10-30 | ||||
| 农场难忘岁月——回忆录(节选)(四)[高诗钢] | 15-10-26 | ||||
| 农场难忘岁月——回忆录(节选)(三)[高诗钢] | 15-10-26 | ||||
| 农场难忘岁月——回忆录(节选)(一)[高诗钢] | 15-10-25 | ||||
| 农场难忘岁月——回忆录(节选)(二)[高诗钢] | 15-10-25 | ||||
| 八五八农场生活追忆(三)[陈光伟] | 15-10-12 | ||||
| 八五八农场生活追忆(二)[陈光伟] | 15-10-10 | ||||
| 八五八农场生活追忆(一 )[陈光伟] | 15-10-02 | ||||
| 牛棚杂忆[王绍才] | 15-10-02 | ||||
| 农场第一天[陈同本] | 15-09-27 | ||||
| 鼓舞—— 忆王震部长视察河南独立分场[蒋述芝张锡林] | 15-09-27 | ||||
下一页
回忆录(节选二)
2015-11-14
作者:八五八农场老兵 唐佽
在北大荒干了十六年
1958年3月28日转业到北大荒农场。到了密山,一上厕所,就吓我一跳:屎尿都结成了冰,大便顶着屁股,根本就没法拉,只好撅着屁股拉一点。第二天,我们就坐敞篷车去驻地。半路上有人叫我:“唐佽,你的行李掉了”。因为天气太冷,我虽听见了,也没有回复,心想;掉了就算了。直到了驻地二队,才从行李里面钻出来。因为太冷,一头扎进住屋里取暖去了。
我们的床,就搭在房东的炕头,是用刚砍下的柞树干搭起来的,上面铺点小叶樟草。他们年轻两口就睡在离我们不远的炕上,我们两个年轻人睡在他们一旁,总觉得不带劲。所以,待天气暖和一点,我就搬到外面苞米楼去了。苞米楼下面一窝老母猪带着小崽,虽有点臭味,也比在小两口旁边窝着强。
没有怎么休息,就开始劳动了。工作就是挖排水沟、脱坯、盖房子,这对我们来讲都是重活,我从来没有干过。回到宿舍,饭都不愿吃就睡了。整天抡十字镐,手指都伸不开。第二天起床,手指得一个一个的掰,才能伸开。就这样,干到7月上山为止。在这期间,有几件荒唐有趣的事。第一件是几万斤水稻种都用“富尔马林”浸泡了,可地还没有翻。我们有个副场长叫曾柯就找几个贫下中农开会,引导他们说:“地不用翻,只要把水田灌上水,把草根淹住就行了(原日本在这里种过水稻,有田埂)。水稻长得快,很快就把草盖住了”。这显然没有道理,大家都不信。这些农工都是南方人,可是没办法,只得服从。如是就把一条裤子的腰给扎住,里面装满稻种,用手把住两裤腿,搁在脖子上边走边撒。这样就出现了“裤播机”的笑话,传遍了整个垦区。
到七月,我就上山伐木了,我是打前站的。到水文站,往里走就没有路了。林子很密,挑着东西根本进不去。我们就扔下扁担,打成被包背着往前走,直到小青山才停住。小青山有一条小溪,我们就在离小溪不远的地方平整了一块地住下。有的砍树搭马架,有的就打草准备苫盖房子,还有的到溪边钓鱼准备晚饭。我们就在这草棚里,地上铺点小叶长樟草睡了。晚上鹿和狗熊来吃尿,我们都不敢吭声。我们在这里,直到路修通了,大量的人上山伐木,才结束修路。伐木很苦,我们这么一批“三门”干部,又没有经验,又没有力气。在这里伐木,伐倒的木头,横七竖八不说,不按规距地伐木,死伤的人也不少。伐木的人,住的是地窨子,天气太冷,烟在地窨里出不来,住在地窨子里的人就得一会儿出来,一会钻进去,像老鼠一样。就这样过了一冬,第二年才砍树盖房子。第三年,我们就下山回八五八农场了。
回到八五八农场,我就毛遂自荐当了中学教师。从此,一干就是十四年。
八五八农场子弟中学从无到有,从茅草房、“穿鞋戴帽”的房子到砖瓦房,从初中到高中,我都参与建设和教学。我带了四个班,其中一个班从初中带到高中毕业。我们一共搬两次家,先在河边,后来搬到基建队,后来又搬回河边。学校开始都是茅草屋,又低又矮又小。好在那时年轻肯吃苦,领着学生什么都干,东边一栋教室就是我领着学生盖的。那时热情高,除教书管学生外,还写诗、填词,还配合学生教育写了好几个剧本。其中写独幕话剧《独生女》就是我一个多礼拜没睡觉写成的,还获得东北农垦总局牡丹江管理局创作奖,在虎林地区演了七、八场。在八五八农场子第中学我什么都敢干,别人不愿干的事或别人干不了的事,我都去干,学校也把我看得很高。我记得杜甫诞生一千三百周年,还让我作学术报告。我为此作了不少准备,看了不少书,从杜甫的出身以及他经历战乱的苦难一生,他的诗作,有关对他的研究评论,我都看了,做了一个多月的准备。越剧“贾宝玉与林黛玉”在电影院上演,因为大家对《红楼梦》了解不多,在放映前要请人讲解一下,我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。为了准备这次讲解,我做了好多准备,《红楼梦》我读了三遍,还看了有关介绍及评论,用了个把月的时间,结果一炮打响。
1966年文化大革命,开始是贴大字报批判“三家村”,接着就是给领导和教师贴大字报。贴我的大字报不少,都是批判我讲课的东西和会上发言。在虎林县集中时,硬要我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,我坚决反驳。结果上面批下来,说我是革命的。回来以后,就是批判游街,我认为这是胡闹。虽然我觉得“造反派”也是忠于毛主席路线的,但我觉得他们作法不对。所以,造反派在学校游斗老师时,他们拽着我,我总是落在老后面。在场部斗人时,有人用铁犁作帽子,我觉得太残忍,看不惯,就不跟他们干。他们就给我戴个帽子:“东郭先生”。我先是站在“造反派”一边,但觉得他们越搞越“左”。后来,他们把一些有历史问题的,有家庭问题的人都带上黑袖标,不准参加革命,每天劳动,晚上集中住在小屋。我看他们太“左”,不符合毛主席所说的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好的”这一教导,所以,我不参加他们的活动。没有事干,我就在家抄大字报。他们两派都拉我,我不偏不依站中间。特别是我到北京以后,看造反派他们乱批乱斗,破坏文物,更是觉得他们不对。回来以后,就什么都不干了,度日如年,盼着文化大革命赶紧结束,好复课。邓副主席提出“复课闹革命”,我兴奋极了,积极紧跟,一直到我调走。
我在汨罗工作四年
1974年5月,我离开八五八农场,调到湖南汨罗文教局。我到湖南汨罗,孤身一人,儿女在北京,老婆在东北,一家三处。我非常苦恼,常常睡不着觉。我在岳阳新墙河开会,三天三夜没有睡觉。长期这样,觉得哪儿都有病,医院的门坎都被我踏破了。其实没有什么病,就是睡不着觉。在教研室,我跟着别人在下面跑,听课、搞调查、开会,有时间还作点指示。我在军队、在北大荒都是别人管着我,在这里,要经常下去巡查,还经常作点指示,我实在不习惯。1978年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高考,我作为汨罗县代表,参加阅卷。我被分配在语文组,担任组长,干了一、二十天,完成了任务。1978年12月我就离开湖南汨罗文教局走了。
在农大干了14年,是我工作的结束地我调来农大,见到儿女,病就好了一半。我到这里,就赶上学校搬回北京,改称北京农业大学。所以我在农场中的农大附中只教了一个多月书,农场的农大附中就解散了,我也调到农大院里的附中。因为我来农大附中以后,表现不错,就任命我为负责人,只搞了一年,就交给地方了。我调到图书馆,刚工作了一个月,说上面有规定,家属在农村的可以调到农场,但男的都要到农场任职。人事处说,农场也算农村,我也得去。这一去,一干就是六、七年。在农场,我当过办公室副主任,当过学校党支部书记。为了儿女,我还在农大自设办事处,干了四、五年,一共浪费了七八年时间。其中农大共借调我四次:一次是清理学校文化大革命,看文化大革命的材料,写学校大事记,下去调查。二是两次搞选举,我都是主力。三是借调到换身份证办公室。在这其间有很多単位要我,可农大不准,只准借,不能调。快到退休了,才调到农业部干部管理学院总院办杂志。
退休前两个月,我到俄罗斯一次,先到黑河,隔着黑龙江,对面就是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,就是历史上的名城——海兰泡。我们住在黑河市农业局,第二天,我们就拎着和俄罗斯人交换的货物过河。先是坐船,上岸后经过检查,到一个俄罗斯人特意为交换货物准备的棚子。棚子里有摊位,把带来的货物同俄罗斯人交换,互相都不知道价钱,换对了换错了,就看你的运气。换了以后,就到一个小餐馆里吃饭。俄罗斯的餐馆比中国差多了,饮料是淡淡的,桌上的菜都是凉的,几片面包就是一顿饭。可他们的街道很宽,屋子有砖砌的,有木头的。但他们人的素质比我们强,穿着、举止、都比我们好,小孩很好看。
回哈尔滨后,我就回八五八农场看看。到农场以后,学校的老教师许凤岐就领着我到处跑,几乎八五八农场所有的地方都跑到了。乌苏里江口岸新建的桥,过货的情况,我们都看了。我原来教的那些学生很热情,都请我吃饭,一个班轮一天,好几天才轮完。过了十多天,我就回学校了。
退休后,在农大院里待了五年,在刘锡恩的公司里混了一年。因为是个皮包公司,后来就不干了。接着,就是我侄儿来了,在农村租了一个房子,合伙生产鹌鹑蛋,送超市。我们合作办厂。后来分开,我们单独干,直到最后倒闭。1997年我搬到育新花园。那时刚过60岁,身体也不错,我们和尹福祥、魏石金、王静天天在一起打麻将,散步,挺有意思。近几年,不行了,我老了。因为脑血栓走路左右晃,我跟他们不能一起玩了。他们还隔三叉五打一次麻将,我就不行了,爬楼都不行了,怕是生命快结束了。
在北大荒干了十六年
1958年3月28日转业到北大荒农场。到了密山,一上厕所,就吓我一跳:屎尿都结成了冰,大便顶着屁股,根本就没法拉,只好撅着屁股拉一点。第二天,我们就坐敞篷车去驻地。半路上有人叫我:“唐佽,你的行李掉了”。因为天气太冷,我虽听见了,也没有回复,心想;掉了就算了。直到了驻地二队,才从行李里面钻出来。因为太冷,一头扎进住屋里取暖去了。
我们的床,就搭在房东的炕头,是用刚砍下的柞树干搭起来的,上面铺点小叶樟草。他们年轻两口就睡在离我们不远的炕上,我们两个年轻人睡在他们一旁,总觉得不带劲。所以,待天气暖和一点,我就搬到外面苞米楼去了。苞米楼下面一窝老母猪带着小崽,虽有点臭味,也比在小两口旁边窝着强。
没有怎么休息,就开始劳动了。工作就是挖排水沟、脱坯、盖房子,这对我们来讲都是重活,我从来没有干过。回到宿舍,饭都不愿吃就睡了。整天抡十字镐,手指都伸不开。第二天起床,手指得一个一个的掰,才能伸开。就这样,干到7月上山为止。在这期间,有几件荒唐有趣的事。第一件是几万斤水稻种都用“富尔马林”浸泡了,可地还没有翻。我们有个副场长叫曾柯就找几个贫下中农开会,引导他们说:“地不用翻,只要把水田灌上水,把草根淹住就行了(原日本在这里种过水稻,有田埂)。水稻长得快,很快就把草盖住了”。这显然没有道理,大家都不信。这些农工都是南方人,可是没办法,只得服从。如是就把一条裤子的腰给扎住,里面装满稻种,用手把住两裤腿,搁在脖子上边走边撒。这样就出现了“裤播机”的笑话,传遍了整个垦区。
到七月,我就上山伐木了,我是打前站的。到水文站,往里走就没有路了。林子很密,挑着东西根本进不去。我们就扔下扁担,打成被包背着往前走,直到小青山才停住。小青山有一条小溪,我们就在离小溪不远的地方平整了一块地住下。有的砍树搭马架,有的就打草准备苫盖房子,还有的到溪边钓鱼准备晚饭。我们就在这草棚里,地上铺点小叶长樟草睡了。晚上鹿和狗熊来吃尿,我们都不敢吭声。我们在这里,直到路修通了,大量的人上山伐木,才结束修路。伐木很苦,我们这么一批“三门”干部,又没有经验,又没有力气。在这里伐木,伐倒的木头,横七竖八不说,不按规距地伐木,死伤的人也不少。伐木的人,住的是地窨子,天气太冷,烟在地窨里出不来,住在地窨子里的人就得一会儿出来,一会钻进去,像老鼠一样。就这样过了一冬,第二年才砍树盖房子。第三年,我们就下山回八五八农场了。
回到八五八农场,我就毛遂自荐当了中学教师。从此,一干就是十四年。
八五八农场子弟中学从无到有,从茅草房、“穿鞋戴帽”的房子到砖瓦房,从初中到高中,我都参与建设和教学。我带了四个班,其中一个班从初中带到高中毕业。我们一共搬两次家,先在河边,后来搬到基建队,后来又搬回河边。学校开始都是茅草屋,又低又矮又小。好在那时年轻肯吃苦,领着学生什么都干,东边一栋教室就是我领着学生盖的。那时热情高,除教书管学生外,还写诗、填词,还配合学生教育写了好几个剧本。其中写独幕话剧《独生女》就是我一个多礼拜没睡觉写成的,还获得东北农垦总局牡丹江管理局创作奖,在虎林地区演了七、八场。在八五八农场子第中学我什么都敢干,别人不愿干的事或别人干不了的事,我都去干,学校也把我看得很高。我记得杜甫诞生一千三百周年,还让我作学术报告。我为此作了不少准备,看了不少书,从杜甫的出身以及他经历战乱的苦难一生,他的诗作,有关对他的研究评论,我都看了,做了一个多月的准备。越剧“贾宝玉与林黛玉”在电影院上演,因为大家对《红楼梦》了解不多,在放映前要请人讲解一下,我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。为了准备这次讲解,我做了好多准备,《红楼梦》我读了三遍,还看了有关介绍及评论,用了个把月的时间,结果一炮打响。

1966年文化大革命,开始是贴大字报批判“三家村”,接着就是给领导和教师贴大字报。贴我的大字报不少,都是批判我讲课的东西和会上发言。在虎林县集中时,硬要我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,我坚决反驳。结果上面批下来,说我是革命的。回来以后,就是批判游街,我认为这是胡闹。虽然我觉得“造反派”也是忠于毛主席路线的,但我觉得他们作法不对。所以,造反派在学校游斗老师时,他们拽着我,我总是落在老后面。在场部斗人时,有人用铁犁作帽子,我觉得太残忍,看不惯,就不跟他们干。他们就给我戴个帽子:“东郭先生”。我先是站在“造反派”一边,但觉得他们越搞越“左”。后来,他们把一些有历史问题的,有家庭问题的人都带上黑袖标,不准参加革命,每天劳动,晚上集中住在小屋。我看他们太“左”,不符合毛主席所说的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好的”这一教导,所以,我不参加他们的活动。没有事干,我就在家抄大字报。他们两派都拉我,我不偏不依站中间。特别是我到北京以后,看造反派他们乱批乱斗,破坏文物,更是觉得他们不对。回来以后,就什么都不干了,度日如年,盼着文化大革命赶紧结束,好复课。邓副主席提出“复课闹革命”,我兴奋极了,积极紧跟,一直到我调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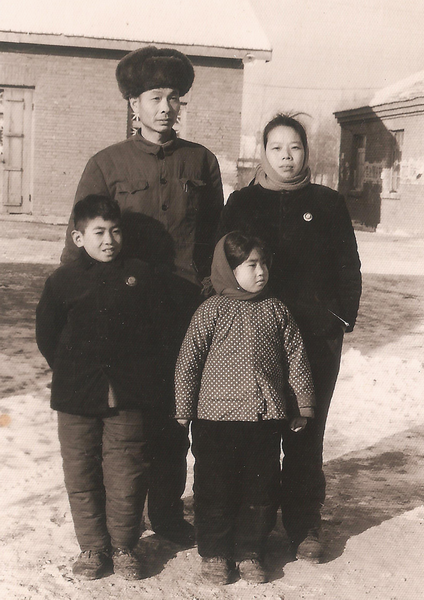
我在汨罗工作四年
1974年5月,我离开八五八农场,调到湖南汨罗文教局。我到湖南汨罗,孤身一人,儿女在北京,老婆在东北,一家三处。我非常苦恼,常常睡不着觉。我在岳阳新墙河开会,三天三夜没有睡觉。长期这样,觉得哪儿都有病,医院的门坎都被我踏破了。其实没有什么病,就是睡不着觉。在教研室,我跟着别人在下面跑,听课、搞调查、开会,有时间还作点指示。我在军队、在北大荒都是别人管着我,在这里,要经常下去巡查,还经常作点指示,我实在不习惯。1978年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高考,我作为汨罗县代表,参加阅卷。我被分配在语文组,担任组长,干了一、二十天,完成了任务。1978年12月我就离开湖南汨罗文教局走了。
在农大干了14年,是我工作的结束地我调来农大,见到儿女,病就好了一半。我到这里,就赶上学校搬回北京,改称北京农业大学。所以我在农场中的农大附中只教了一个多月书,农场的农大附中就解散了,我也调到农大院里的附中。因为我来农大附中以后,表现不错,就任命我为负责人,只搞了一年,就交给地方了。我调到图书馆,刚工作了一个月,说上面有规定,家属在农村的可以调到农场,但男的都要到农场任职。人事处说,农场也算农村,我也得去。这一去,一干就是六、七年。在农场,我当过办公室副主任,当过学校党支部书记。为了儿女,我还在农大自设办事处,干了四、五年,一共浪费了七八年时间。其中农大共借调我四次:一次是清理学校文化大革命,看文化大革命的材料,写学校大事记,下去调查。二是两次搞选举,我都是主力。三是借调到换身份证办公室。在这其间有很多単位要我,可农大不准,只准借,不能调。快到退休了,才调到农业部干部管理学院总院办杂志。
退休前两个月,我到俄罗斯一次,先到黑河,隔着黑龙江,对面就是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,就是历史上的名城——海兰泡。我们住在黑河市农业局,第二天,我们就拎着和俄罗斯人交换的货物过河。先是坐船,上岸后经过检查,到一个俄罗斯人特意为交换货物准备的棚子。棚子里有摊位,把带来的货物同俄罗斯人交换,互相都不知道价钱,换对了换错了,就看你的运气。换了以后,就到一个小餐馆里吃饭。俄罗斯的餐馆比中国差多了,饮料是淡淡的,桌上的菜都是凉的,几片面包就是一顿饭。可他们的街道很宽,屋子有砖砌的,有木头的。但他们人的素质比我们强,穿着、举止、都比我们好,小孩很好看。
回哈尔滨后,我就回八五八农场看看。到农场以后,学校的老教师许凤岐就领着我到处跑,几乎八五八农场所有的地方都跑到了。乌苏里江口岸新建的桥,过货的情况,我们都看了。我原来教的那些学生很热情,都请我吃饭,一个班轮一天,好几天才轮完。过了十多天,我就回学校了。
退休后,在农大院里待了五年,在刘锡恩的公司里混了一年。因为是个皮包公司,后来就不干了。接着,就是我侄儿来了,在农村租了一个房子,合伙生产鹌鹑蛋,送超市。我们合作办厂。后来分开,我们单独干,直到最后倒闭。1997年我搬到育新花园。那时刚过60岁,身体也不错,我们和尹福祥、魏石金、王静天天在一起打麻将,散步,挺有意思。近几年,不行了,我老了。因为脑血栓走路左右晃,我跟他们不能一起玩了。他们还隔三叉五打一次麻将,我就不行了,爬楼都不行了,怕是生命快结束了。
[唐佽]